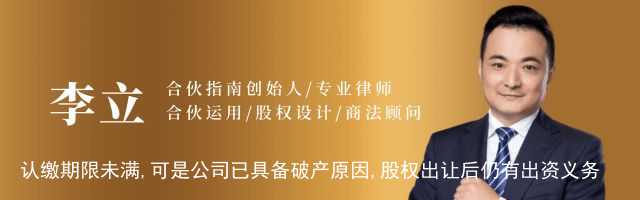
合资经营手册 | 译者:富子梅辩护律师
这是富子梅辩护律师网志和合资经营手册第998篇文本
认缴时限年满,不过公司已具有宣告破产其原因,股份卖地后仍有出资权利
一
这是个还有争论的法律条文公法难题。
股东在把自己的股份受让进来的时候,认缴时限还没到,也没提早实缴,所以,当股份受让顺利完成后,该些股份的出资权利可否分担呢?是仍由卖地方承担,还是由受让来履行职责呢?
各省市人民检察院的裁决中,认知是并不标准化的。
往后,我见过有的是高等法院裁决即使认为出资权利是跟随着股东那个身分的,因此,股东把大部份的是股份都受让进来了,已经不具有该公司股东身分了,所以也就无须分担出资权利了,股份受让后的出资权利由受让分担。
所以,法律条文和判例是怎样明晰规定的呢?
《公司法》其中的法律条文,为此并没明晰的明晰规定。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发布的判例中,有“密切相关”的许多明晰规定。但,判例的明晰规定,或许让那个难题又多了些捷伊争论认知的难题。
《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司法>若干个难题的明晰规定(三)》明晰规定:
第二十一条以下简称公司的股东未履行职责或是未全面性履行职责出资权利即受让股份,受让人为此晓得或是应晓得,公司允诺该股东履行职责出资权利、债务人为此分担控股股东的,人民检察院应予以全力支持;公司债务人依本明晰规定第十一条第三款向该股东提出诉讼民事诉讼,同时允诺上述债务人为此分担控股股东的,人民检察院应予以全力支持。债务人根据第六款明晰规定分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职责或是未全面性履行职责出资权利的股东追讨的,人民检察院应予以全力支持。但是,原告梅塞县签订合同的仅限。就是下面这条判例,也历经了一个从存在许多严重错误认知到标准化正确认知的过程。
这条判例在正式发布后,曾有一两年,有些人对“未履行职责或是未全面性履行职责出资权利即受让股份”的认知产生了严重错误,严重错误地认为认缴时限未届满时受让股份,也属于“未履行职责或是未全面性履行职责出资权利”。
目前,人民检察院在这条判例的认知方面已经基本达成了标准化的观点,即认缴时限未届满时受让股份,不属于这条判例里的“未履行职责或是未全面性履行职责出资权利”。
说实话,这样的严重错误认知是不该出现的,因为并不复杂,只要根据整份判例的文本就能得到准确的认知。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司法>若干个难题的明晰规定(三)》这份判例里,“未履行职责或是未全面性履行职责出资权利”,这是一个多次出现的表述。只要看一下另一个条款,就能明白那个词组的准确含义:
第十一条股东未履行职责或是未全面性履行职责出资权利,公司或是其他股东允诺其向公司依法全面性履行职责出资权利的,人民检察院应予以全力支持。公司债务人允诺未履行职责或是未全面性履行职责出资权利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分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检察院应予以全力支持;未履行职责或是未全面性履行职责出资权利的股东已经分担上述责任,其他债务人提出相同允诺的,人民检察院不予全力支持。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职责或是未全面性履行职责出资权利,依本条第一款或是第三款提出诉讼民事诉讼的原告,允诺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分担控股股东的,人民检察院应予以全力支持;公司的发起人分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讨。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职责或是未全面性履行职责出资权利,依本条第一款或是第三款提出诉讼民事诉讼的原告,允诺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明晰规定的权利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分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检察院应予以全力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分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讨。从第十三条的内容来看,“未履行职责或是未全面性履行职责出资权利”是一个违法行为,是可以被立即追索的行为,那个表述一定是不包括“仍在认缴时限内而没实缴”的情形,因为:在认缴时限内而没实缴,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股份的权利。
因此,该判例第二十一条,并不是针对“认缴时限未届满时股份受让,可否分担出资权利”的难题。
转了一圈,发现那个难题并没明晰对应的法律条文明晰规定和判例,于是,就产生了不同的认知和裁决。
二
有哪些不同的认知和裁决呢?
有的是认为卖地方,也就是原股东在股份卖地后,仍然应履行职责原来的出资权利。而有的是认为原股东在股份卖地后,出资权利也就相应地转移给了受让,原股东无须分担原出资权利。
所以,目前,高等法院在公法中究竟是怎样认知那个难题呢?
通常来说,高等法院首先要考虑是不是存在两个特殊的情况:
有没“出资加速”的情形;有没“故意逃债”的情形。所谓“故意逃债”,就是故意将股份受让给明显没出资能力的债务人,以达到实际不用履行职责出资权利的效果。有关这一点,目前高等法院实际裁决的很少。但,未来这必然会成为司法的一个关注点。这一方面,今天就略过不聊了。
重点来说说“出资加速”。
所谓出资加速,是指法律条文明晰规定的“出资加速到期”、不受原来公司章程签订合同的出资时限的限制。
根据法律条文和判例,“出资加速”的情形有:
公司进入宣告破产程序时。《企业宣告破产法》第三十五条明晰规定“人民检察院受理宣告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职责出资权利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时限的限制。”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检察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有宣告破产其原因,但不申请宣告破产的,债务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允诺未届出资时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分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检察院应全力支持。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时限的,债务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允诺未届出资时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分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检察院应全力支持。上述第2、3点,是最高人民检察院2019年正式发布的《全国高等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6条中明晰规定的内容。
根据上述“出资加速”的明晰规定,在实践中已经在各省市高等法院都有许多实际裁决了。
但,今天本文标题的那个论点,是来自于一个实际的高等法院裁决。那个观点,是对现有的是普遍的司法认定的一个小小突破。
那个裁决的新意在于:把“出资加速到期”视作是一种因事实而产生的法律条文权利,而不是把它视作是公司债务人向高等法院主张允诺权而产生的法律条文权利。
也就是说,现在的常规认知是:只有在公司债务人向高等法院提出诉讼民事诉讼,并且高等法院裁决公司股东以出资加速到期的方式对公司债务分担相应赔偿责任时,才产生了公司股东必须出资加速到期的权利。
不过,在下面要说的那个裁决中,高等法院认为只要事实上公司具有了宣告破产其原因时,那时公司的股东们就已经产生了出资加速到期的权利。
三
2020年1月,原告甲公司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检察院起诉。主要民事诉讼允诺是:
判令A公司向乙公司支付未缴出资款人民币440万元(以下币种同)并分担逾期利息(以44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10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判令B公司、C公司对上述第一项付款权利分担控股股东。来理一下这些原告之间的关系:
甲公司是乙公司的宣告破产管理人。A公司是乙公司原来唯一的股东,后来将乙公司的股份分别受让给了B公司和C公司因此,甲公司的民事诉讼允诺,就是乙公司的宣告破产管理人要求已经因受让股份退出乙公司的原股东A公司向乙公司缴纳出资款。
2019年9月10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检察院裁定受理对乙公司的宣告破产清算申请。宣告破产管理人甲公司查阅原告工商内档及查询公开信息,至A公司受让股份前仅实缴注册资本60万元,仍有440万元未缴纳。B公司、C公司明知A公司未实缴出资的情况,且在受让股份后亦未继续缴纳注册资本。
于是,宣告破产管理人甲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企业宣告破产法》第三十五条的明晰规定向高等法院提出了此次民事诉讼。
一审高等法院全力支持了原告的民事诉讼允诺。二审高等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此案高等法院的认定逻辑是:
股份受让前公司已具有宣告破产其原因,因此,A公司的出资在股份受让前既应认定加速到期;乙公司在具有宣告破产其原因的情况下并及时申请宣告破产清算,作为当时乙公司唯一股东的A公司未积极推动乙公司申请宣告破产清算,也未积极缴纳出资补充公司资本用以清偿债务。此种情形下,为维护乙公司债务人之利益,应比照《企业宣告破产法》第三十五条之明晰规定,认定股东未届出资时限的出资因公司具有宣告破产其原因而加速到期,暨认定A公司在受让股份之前其出资权利应加速到期。A公司的出资因加速到期而应被认定为瑕疵出资并分担瑕疵出资责任。A公司就出资权利已应加速到期的股份再行对外受让,属于瑕疵出资股份受让,其出资权利不得因股份转让而解除,乙公司仍有权要求其履行职责出资权利。依《公司法判例三》第二十一条之明晰规定,A公司仍应对乙公司440万元的出资部分履行职责出资权利。那个案件的裁决突破了以往的法律条文认知,但考虑到此案的具体情形,裁决结果反而显得较为合理。但,在公法中,那个案件的认定逻辑能否复制到具体情形有所不同的其他案件中呢?建议还是采取较为保守的态度来看待为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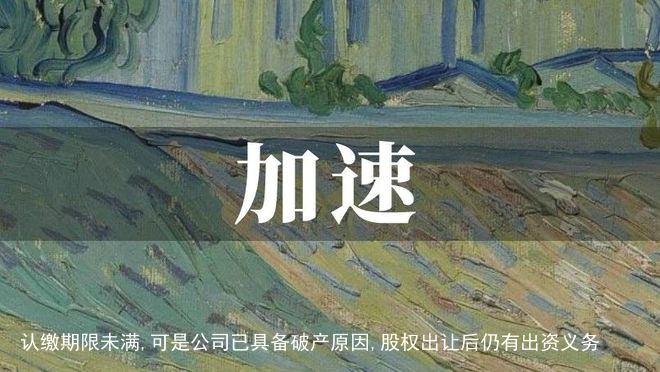




咨询热线
0755-86358225